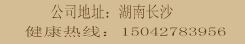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人口民族 > 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人口民族 > 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

![]()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人口民族 > 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人口民族 > 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
专注分享学习,一站式获取海量语言学资源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梁国杰
():作者简介李安山,北京大学荣休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摘要: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区城国别研究(简称“地区研究”)表现出特有的兴趣。这与开放程度扩大、民众知识面扩展和好奇心增加相关,也与中国外交直接关联。本文追溯了地区研究的历史传统,认为地区研究缘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非美国制先,而是具有久运的传统,现代地区研究在英国已有先例。地区研究并非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咨询为主要任务,其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国民视野、借鉴他国经验、推进学科交流和咨政辅助作用。这应是中国地区研究的特色所在。随着学术交往加深,学界认识到地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单独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地区研究需要实地调研、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语言学习,跨学科、比较研究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的借鉴。地区研究应该也必然推动学科交流和相互渗透,为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区城国别研究地区研究研究传统跨学科语言学习咨政
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其文明的态度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容纳还是排斥,是学习借鉴还是歧视贬低?这实际上是检验任何一种文明的生命力的最好标准。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明的精粹而集大成。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与教育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以下简称为“地区研究”)表现出特有的兴趣。一方面,这与中国近年开放程度扩大、民众知识面扩展和好奇心增加相关,同时也与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直接关联。这里的地区研究是指对某一国家成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的全方位、跨学科研究,牵涉到地区确定、资料收集、语言培训、综合研究及政策建议等多方面内容。其特点包括对掌握当地语言和实地调研的重视、强调研究与教学的有机结合、建立跨专业领域的学术团体、注重对象国(区域)历史与当代问题的关联、专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等。
本文将集中就中国地区研究的传统、目的与方法发表浅见。作者遍溯了全球特别是中国地区研究的历史传统,提出了自己对地区研究之目的的看法;认为地区研究缘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并非美国创先,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现代地区研究在英国已有先例。本文不赞成地区研究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提出地区研究有四个目的:扩大国民视野、借鉴他国经验、推进学科交流和国家战略的咨政辅助作用。这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研究。最后,作者就地区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地区研究的历史传统
学界多将地区研究的缘起归结于冷战或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公布。这种解释有欠公允,这一观点实源于二战后美国影响力迅速提高及地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快速发展。地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确实与美国有关,但其传统远早于冷战。学术史表明、人类对其他地区的好奇、了解与研究由来已久。如果从古代以来人类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探索和记载算起,地区研究大致具有六种历史传统——古代学者的研究、地理大发现时旅行家的游记和思考、传教士的报告、启蒙运动时期的探讨、殖民时期的调研及一战后对人类命运的担忧而催生的学术研究。
近代以来的地区研究与文明探讨相结合,受各种偏见特别是我族中心主义(ethnoeentrism)或国家中心主义的影响,为殖民主义扩张服务,其研究的客观性大打折扣。西方有关其他地区或民族的著述多以欧美中心论为基轴,有关文明概念的偏见甚多。本人认为,文明用物化标准来衡量是极其片面的。近代以来的“文明”概念被政治化。首先,人的发展受当地环境的影响,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文明成果(例如,犁/轮子/驯养/建筑/城市/语言/武器/冶炼等)。其次,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为了替殖民主义扩张寻求合理化依据,“文明”概念被长期政治化,成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压迫和剥削其他民族的工具,世界民族也因之被人为地分为“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其他地区或民族)”。本人尝试从人类历史视角为文明定义:文明是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包括解决与自然之矛盾的方式,与他人共处的方式和调解自身问题的方式;文明具有多元、整体、言语和嬗变(积淀和修正)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文明”概念存在悖论:“文明”的民族破坏自然的手段更先进,自相残杀或破坏人类文明的手段更高超,自杀率相对较高。由于两方对地区及别国文明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学术界借鉴有关研究成果时应该格外注意。
早在美国提出地区研究计划之前,日本、英国、法国等在殖民时期对地区研究已有实践。设立于年的满铁调查部专门从事对中国东北全境(后来有所扩展)的调研,任务是充分了解和考察该地区的社会风俗习惯、经济特点、交通与历史地理状况,目的是支待日本“经营满洲”的侵略政策,这是典型的地区研究,缺少的只是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年,英国政府设立以雷伊勋哥为首的委员会探讨英帝国东方学的状况,委员会曾建议伦敦大学开办东方学院以培养政治、商业、外交和学术上的精干专家,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实现。直到年2月23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创立,年改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简称S0AS),简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应该是以高校为单位进行系统地区研究的发端。从机构设置、学校管理、教学领域、课程安排、人才培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践行地区研究模式,特别是注重语言训练及教学研究相结合。早期,英国针对非洲的知识生产以社会人类学为主,授课对象主要是殖民官。一批批殖民统治官员就是通过系统培训后派往殖民地的。这些人因为兼有殖民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其研究虽带有偏见,但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不同学科的理论指导,二是在殖民当地的成果产出对后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员拉特雷是一个典型例子。年,英国殖民部曾授意剑桥大学为非洲殖民官员开设研究生课程,之后又设立暑期非洲课程。这些机构、学校、课程和项目创立的目的是培养殖民统治所需人才及对殖民地精英进行同化教育和训练。这些传统为二战以后因亚非国家独立和以美苏争霸为特点的冷战而兴起的地区研究打下了基础。美国地区研究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三点。一是以国家法律作为支撑以保证其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二是将地区研究纳入全国教育体系来通盘考虑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三是通过加强对象国语言教育来深人研究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
中国的地区研究也有厚重的历史传统。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以及资料的收集。正史均记载关于边塞及中外交往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当今国人对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认识即建立在早期所收集的资料这一基础之上。自《史记》始,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可谓资料不菲。《史记》中以列传的方式记述了汉代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民族历史、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史记·大宛列传》以张骞通西域所得,描述了中国西部边疆甚至中亚地区诸国的地理位置、习俗与文化。“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麓陶酒。有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廓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打梁、于寞。”“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奴,及雪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芜,号小月氏。”这是中国早期的地区研究资料。二十四史皆然。在《汉书》的《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中,资料较《史记》更丰富。随着国人对外界认识的提高,中国对外交往的半径日益加大,正史中这些与外部地区相关的资料不断补充完善。
相关地区资料不断积累,多为通过旅行记载及对外交往所得,从周边逐渐扩展至其他地区。东晋高僧法显(一年)在65岁高龄时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交通交流的重要史料。由唐代玄奘(一年)口述、辩机所编、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年)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两百多个国家和城邦及诸多民族。杜环(生卒年不详)为《通典》作者杜佑之族子,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年)在但逻斯河战役兵败,被大食人所俘。十余年后,宝应初(年)经海路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经行记》已亡佚,仅散见于《通典》边防典中的多字。杜环对摩邻国描述道:“又去摩邻国,在秋萨罗国酉南,渡大碱,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鹤莽,鹊莽即波斯枣也。律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威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滤浪终日。”对“摩邻国”究属何地,学界的解释多达10种。段成式(?一年)的《酉阳杂俎》,记载了拨拨力国(今索马里)的物产和风土人情。该书还记载了其他国家如“孝亿国”、“仍建国”、“悉但国”、“勿斯离国”、“甘棠”等。据考证,孝亿为今埃及南部,仍建为突尼斯,悉但似指今日之苏丹,勿斯离为埃及,甘棠为非洲东海岸。
宋代周去非(-年)在《岭外代答》(年)卷二的“海外诸番国”和卷三的“航海外夷”这两条中,将所知位于南方和西方的海洋分为几个海域,如“交趾海”、“南大洋海”、“东大洋海”、“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等。其中的“西大食海”地处最西面,所指即今地中海,其航线可通木兰皮国(今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卷三记载有“昆仑层期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婴。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熟钢铁与之食。及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善奴。”对于“昆仑层期国”之所在,一般认为在东部非洲,但就其确切位置尚存分歧。张星焕认为“昆仑层期国”即桑给巴尔,但比现在的桑给巴尔范围要大得多,为“古代东非海岸通称”。有学者认为,它是指马达加斯加岛及其附近的东非海岸。在中国人对非洲了解不多的情况下,对东非海岸及相邻地区统称为“昆仑层期”是可以理解的。赵汝适著《诸藩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东部非洲的资料。“层拔国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继青番布,碾红皮鞋。日食饭面烧饼、羊肉。乡村山林,多障岫层叠。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人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根据考证,层拔国为今桑给巴尔(Zanaihar)。“大山”是指东非的乞力马扎罗山。
资料收集以亲身经历为要。与前人不同,元代汪大渊两次航海远游,游历南洋群岛和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他留下的笔记《岛夷志略》(年)记录了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不失为地区研究的新资料。元代未思本(-年)曾绘制了一幅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画中已出现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此地图已铁,只能在明代罗洪先增补的《广奥图》中见到。现存“大明混一图”(年)表明了当时国人的地理知识水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自此更有增扩。一些重要的中外交通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地区研究特别是资料收集的水平大大提高,包括费信的《星搓胜览》、马欢的《流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例如,费信对“竹步国”记载如次:“竹步国,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地产勇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米、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文中除对竹步国的位置、民居、气候、生产、风俗、物产有所记载外,最后还提到当地的首长因收到郑和船队所赐礼物,深受感化,奉贡物产,以结友好,记录颜为细腻。由于三人均随同郑和出使外国,其著作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描述更具史料价值。
清代随着传教士日增和国门打开,对外交往加深。传教士的影响是双向的。传教士“把一个开明的中华帝国的形象带回欧洲”,从而构建了一个幅员阔又强大富庶的中华帝国的神话。传教士既为中国带来了异城风俗和地理知识,也带来了偏见,总体上促进了民间与外界的交往,也触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外观念的转变。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处理外务的过程中不仅力图保持天朝帝国的威严,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紧迫性。他在英人《世界地理大全》基础上编译的《四洲志》涵盖亚、欧、非和拉美四个洲的3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北非、西非、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向国人介绍了作为整体的世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国人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文化有了初步认知。正史也因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清史稿》中出现了“邦交志”,列举了清王朝与19个国家的邦交关系,即与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日本、瑞典、那威(挪威)、丹墨(丹麦)、和兰(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义大里(意大利)、奥斯马加(奥匈帝国)、秘鲁、巴西、葡萄牙、比利时、墨西哥、刚果的邦交关系。在《清史稿·属国传》中则记录了中国与相邻属国的关系。这正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应对之策或无奈之举。因应时势变化,民国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方面。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l-):政治》,世界各国政治中以中国政治居多(种);比较政治为种,外交和国际关系为种,两种共占总书目的20%。比较政治的著述多从宏观角度着手,对政体、选举、宪法、政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国别政治研究集中在故美等发达国家,如樊德芳的《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年)、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年)、兼文哲的《法西斯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年)、黄子度的《现代德国政治》(年)、金长佑的《日本政府》(年)等。对苏联的研究包括胡庆育的《苏联政府与政治》(年)和林孟工的《现代苏联政治》(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忙于经济恢复,加之处于外国势力封锁之下,中国地区研究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开始。年12月30日,中国政府指定三所重点大学负责重点研究地区国别:复旦大学负责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学负责研究社会主义阵营,北京大学因具有人文科学特别是多种东方语言的优势,专门负责亚非地区的研究。除了大学之外,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研究机构也随之成立,如亚非研究所成立于l年7月4日,并处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外事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下。年,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亚非研究所拥有两份内部刊物,《亚非译丛》(始于年,主要是翻译亚洲和非洲的著述)和《亚非资料》(始于年,主要是关于亚季的资料)。这应该是中国系统的地区研究的开始。“文革”的冲击使中国学术研究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重新恢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需要大量熟悉外国历史和现状的人才,从面向人文社会科学提出新要求。由于长期与国外学术界隔绝,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人才不足和不请国际学术发展的困境。由于对学科定位知识缺乏了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之后,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提出过建立‘美国学”‘日本学”“非洲学”等学科的主张”,这与英语的“shudies”和“discipline”均译成“学”有关,如“美国学”(ArnericsnStudies)。随着与国际学术界交往加深,学界逐渐认识到地区研究的学术特点:“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
总之,中国从古代到当代,一直试图认识外部世界并收集资料,
转载请注明:http://www.ougeccar.com/rdmz/5110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