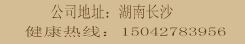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周末文学萨宾娜的心愿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周末文学萨宾娜的心愿

![]()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周末文学萨宾娜的心愿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周末文学萨宾娜的心愿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Tokarczuk,—)是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赞她“运用观照现实的新方法,糅合精深的写实与瞬间的虚幻,观察入微又纵情于神话,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独创性的散文作家之一”。
托卡尔丘克是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一个中欧小国再一次因了文学而受到世界的瞩目。这是文学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萨宾娜,是M医生家里的清洁工。M医生和妻子尤拉相亲相爱,夫妻俩育有一小女儿,名叫卡齐娅。这几年来,萨宾娜每周一次准点来到M医生家打扫卫生,到目前为止,估计已不下几百次了。
每一次打扫的流程都大同小异:首先是医生的接诊室、女病人专用候诊室、卫生间,再轮到客厅、饭厅、宽敞的厨房以及楼上的卧室——其中一间是医生夫妇俩的,另一间是小卡齐娅的。每逢节假日、周末连休或命名日(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萨宾娜需额外打扫一下客房,但这种情况较少发生。此外,房子的前庭和后院各有一个露台,萨宾娜时不时要清扫落叶和刷洗瓷砖。
据估计,萨宾娜每年要进行常规打扫五十多次,将所有的窗户彻底清洁五到六次,还要给红陶地板除尘、抛光二十余次,将地毯拿到院子里,用力拍打以除尘——大概三到四次。正因为如此,萨宾娜对房子里的每个角落,房子里的每件家居用品都了如指掌。
她对房子里的物品既有爱也有恨,喜欢结实耐用的原木餐桌,也喜欢落地灯的彩绘玻璃灯罩,但无法接受壁炉旁的那些黄铜锅,极其讨厌永远也刷不干净的炉灶,但是,她最爱的还是卡齐娅卧室里的粉色地毯,还有浴室里一尘不染的白色瓷砖。
每周五,是萨宾娜到M医生家做工的日子,她会在周四时特意多准备一些馅饼,这样她不在家时,儿子饿了,只需要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填饱肚子了。这一天,医生一家通常会煎鱼吃,如果煎得不好,平底锅可能会烧焦,萨宾娜就得把锅刷干净。
天还没亮,萨宾娜就得出门,从她住的山麓区出发,红色的早班公交车直达M医生宅邸前。这趟车从萧条破败、气味难闻的山麓区出发,直达绿树成荫、茉莉花开的什察弗纳区,穿过瓦尔布日赫市的大街小巷,就像是郊游一样,萨宾娜一直都很享受这趟旅程,她只希望,这趟旅程不要这么快结束。萨宾娜总是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当车上乘客较多时,她还会坐在爱心专座上——因为,她怀孕了。
其实,萨宾娜对怀孕早已习以为常,毕竟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准确地说,是五个儿子!怀孕是萨宾娜再自然不过的状态。她怀孕时,从不会感到头晕作呕,也不会性情大变,口味更不会和往常有什么不同,而且身材既不变胖,也不变瘦。
萨宾娜从来就不怎么在意自己的身体,早上出门前给这具躯体套上一件廉价运动服或印花棉布连衣裙,就可以把这副模样维持到夜晚上床睡觉前。漫长的一天,这具躯体虽有布料掩盖,但也会表现出难以控制的生理需求,但一般情况下,她并不需要把过多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体上。
但最近,尽管不常见,当萨宾娜在尤拉卧室里打扫时,她还是忍不住在大镜子前观察自己的身体,她想看看,自己的肚子和平常相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众所周知,如果怀的是女孩,妈妈的肚子会显得更加宽大圆润,呈拱顶形;如果怀的是男孩,肚子则会向前凸出,像指向天空的塔尖,摸起来如足球般坚硬。
不久前,尤拉在无意中发现了萨宾娜这一异常举动,萨宾娜猝不及防,十分尴尬,脸颊通红,赶紧假装在擦镜子。“怀孕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夫人说道,“怀孕时的你看起来更漂亮呢。”
萨宾娜在收拾医生夫人随手扔在沙发上的衣服,她小心翼翼地把衬衫和裙子搭在肩上,就好像这些衣服是会奔会跳的小动物似的。她把衣服挂在衣柜的木架子上,夫人的衣橱香气扑鼻,这是一种无名鲜花怒放时的芳香,这是夫人身上散发的女人味,一种夫人特有的清新恬淡,却又充满诱惑的气味。
相比之下,萨宾娜不太乐意整理医生的衣服。即使医生的衬衫和外套的质地和夫人的裙子一样柔软,但是萨宾娜在碰他的衣服前,双手总会不由自主地在空中定格半秒钟。她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地犹豫,但是该完成的任务还是要完成。但究竟为何手部会不由自主地抵触呢?难道是因为她联想起了男人脸颊上扎人的胡茬子?男人粗糙的双手?又粗又硬的眉毛?爬楼梯时沉重均匀的脚步声?身上挥之不去的酒气?
萨宾娜把衣服都整理叠放好后,关上衣橱的推拉门,离开前再打量了一下门上镜子里的自己。
正当萨宾娜收拾好医生的卧室时,前厅传来了小女孩的声音,小卡齐娅放学回家了。萨宾娜停下手头的活儿,跟随尤拉到楼下去迎接卡齐娅。
卡齐娅坐在地板上,边解鞋带,边回应着妈妈的唠叨,并对萨宾娜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卡齐娅的缕缕金发,微微卷起,柔软顺滑,沿着额角披垂下来,遮住雪白的脖子。小女孩脸蛋上长着雀斑,两只眼睛像蓝宝石般清澈透明。她的嘴唇线条分明,如同两片薄薄的花瓣儿,就是略显苍白,这张可爱鸟儿的小嘴巴,与其说是为了吃东西而生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吟唱婉转悦耳而生的。她的牙齿并不小——所以声音显得更加动人——萨宾娜心里这样想。
萨宾娜帮卡齐娅把书包拿到楼上去,放下书包后,开始打扫卡齐娅的房间。在此期间,卡齐娅会吃午饭。饭后,家庭教师会带着两个邻家小女孩来到医生家,和卡齐娅一起上英文课。他们总在楼下的客厅上课,萨宾娜隐约能听到老师和女孩们交谈的声音,有时还会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陌生的、断断续续的、不知所云的低沉喉音。萨宾娜唯一能听懂的词就只有“yes”了,但她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卡齐娅上课期间,也是一天当中萨宾娜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卡齐娅的房间,卡齐娅的房间,光是听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联想起美味的甜蛋黄(中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一种甜品,成分包括生鸡蛋黄、糖、蜂蜜等)和芝麻蜂蜜糖。
卡齐娅的房间,是粉色的,是粉色的世界。当萨比娜踩着软绵绵的地毯时,对神灵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她要是穿着鞋子,是绝不敢踏入卡齐娅的卧室半步的。她双膝跪在地毯上,耐心地把地毯上一块块小积木、饼干屑捡起来,然后开始除尘,起码要两三次她才放心。
有时,萨宾娜会感到……怎么说呢,虚弱或者悲伤——萨宾娜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萨宾娜会感到……唉,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总之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萨宾娜会躺在粉色地毯上,侧着身子,这样肚子就没那么难受,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
当她躺在地板上时,她觉得房间变得更有安全感,更加温馨。她完全可以一直这样躺着,用指尖触摸着地毯的粉色绒毛,身体逐渐暖和起来,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无忧无虑地做着白日梦,在梦中,所有思绪都在不断流动,不断改变自己的位置。“是的,是的,”楼下传来小女孩说着的英语。萨宾娜得赶紧起身了,否则活儿就干不完了。
她给卡齐娅换了副被套,即使被套如此地洁净无暇。她还花了很长时间来揉按枕头,好让它完美地契合卡齐娅的头形。她还用手拍打被子,这样羽绒会变得均匀、蓬松些。最后,萨宾娜饶有兴致地思量应该选哪个枕套——卡齐娅的衣橱里各种枕套一应俱全:有粉色带雨伞图案的,浅蓝色带小象图案的,还有纯白色丝质的,粉红色绸缎的,像冰面一般光滑的,以及丁香树枝压纹纯棉质地的。
萨宾娜开始收拾小女孩的书桌。她把蜡笔、卷笔刀、写满潦草文字的笔记本都逐一整理归类。她把吃剩的苹果,扔得满桌子都是的糖果纸、橘子皮都放进垃圾箱,然后再用抹布把桌面的灰尘擦拭干净。她将玩具娃娃有序摆放到小床和小车上,给每个娃娃穿上鞋子,拉上裙子的拉链。对萨宾娜来说,这是每周五最美妙的时刻——她能亲手抚摸这些娃娃,拨弄她们的头发,将她们摆到架子上。
萨宾娜此时此刻并不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她很清楚,自己的手指太僵硬了,甚至还有点肿胀,根本无法给娃娃系裙带或拉拉链。每当此时,尤拉都会以找各种东西的名义走进卡齐娅的房间,实际上是不放心让萨宾娜一直待在自己女儿的房间里。
“萨宾娜,怎么说呢,行为好像有点孩子气,”尤拉跟丈夫聊起萨宾娜,“我看见她在玩娃娃。”
“别开玩笑了,”M医生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告诉她,她该来抽个血了,这样我下周还能检查她的血红蛋白。”
尤拉说:“你本可以给她开避孕药的。”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开药的速度都赶不上她怀孕的速度。你不如让她来做个超声波检查吧。”
现在,整个房子看起来井井有条。萨宾娜终于可以在厨房休息一会儿了,她给自己沏了杯热茶,端上一盘饼干,有时会在饼干上敷点糖粉,有时撒点椰蓉。医生夫人穿着紧身裤,她一直都在节食减肥,但还是忍不住尝了一小口。
两人的聊天断断续续,萨宾娜聊起她的五个儿子,年龄最大的儿子已经在上技校了,最小的仍在蹒跚学步。尤拉老是记不住萨宾娜五个儿子的名字,但出于礼貌,她会注意措辞,不提起他们的名字。
尤拉在聊天时特别谨慎,尽量不问及萨宾娜丈夫的事情,即使她知道,萨宾娜肯定会闪烁其词地说,丈夫是个老实人,工作很努力,帮忙挂窗帘,烤蛋糕,还在他们家铁路旁的院子里种西红柿,每周日全家都上教堂去参加礼拜,偶尔还一起去郊外湖边度假,孩子们可以在湖里游泳。当然,还会说他不喝酒。不,她应该不会说他不喝酒。她根本就不会提起酒这个字,也不会提起别的事情。只要不提起,这些事就当没发生过。
萨宾娜不是生来就不善言辞,而是大量训练的结果。在言语被道出前,先把它们吞下去,这是一种难得的技能。两人待在一起时,尤拉总会忍不住偷看萨宾娜。萨宾娜拿起水杯时,她的双肩显得有点异常,看起来更窄些,弱不禁风。
茶喝完后,该熨烫衣服了。萨宾娜将一大摞刚洗干净、有点发硬的衣服、抹布、毛巾、被套、枕头套摆到面前,开始熨烫。她还要把每双袜子配对,并折叠成球状。她还得把褶皱的床单重新压平整。如果衣服的纽扣被洗掉了,她会把相同颜色的缝上。萨宾娜在熨衣板旁度过几个小时,直到夜幕悄悄降临。
小女孩们与老师道别后,便活蹦乱跳地跑到楼上玩耍。另外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长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另一个头发呈暗黄色,小脸蛋胖乎乎的。她们在楼梯上约定好游戏规则,在她们眼中,游戏里的世界就是全部。今天我来扮布兰卡和吉普赛人,你来扮公主和苏珊娜。你来当老师,我来当医生。你带孩子来我这儿看病。还是不了,让我们来玩过家家吧。每个人都有一座大房子和孩子。我邀请你们来我家烧烤。我们一起去突尼斯旅游。
萨宾娜在一旁看着小女孩们玩耍,熨斗划过衣服,留下一道道光滑的痕迹,每一处褶皱都变得平整。
小女孩们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用小手划分出不同的边界。如果有人越过了这些看不见的边界,就要说“您好”,记得一定要在姓氏后加上“女士”两个字。
萨宾娜看着她们把娃娃放在粉色地毯上,把萨宾娜刚刚才绑好的裙带解开,没一会儿,娃娃的衣服就被脱光了。啊,别,别脱光啊!娃娃可不能不穿衣服!不穿衣服的芭比娃娃就像昆虫一样瘦削,肌肤粉嫩、紧致。娃娃可不能不穿衣服啊,因为娃娃没有内外之别,这使得她们看起来如同宝石一般完美。
女孩子们一直滔滔不绝,萨宾娜已经没有在听了,其实她并不关心女孩们说话的内容,她专注于她们像鸟儿歌唱一般的嗓音,其旋律层次丰富,甜如浸蜜,能欣赏这般天籁之音,萨宾娜已别无所求。她熨烫衣服的节奏逐渐慢下来,像机器人一样。熨斗下的床单甚至都觉得有点无聊了。
如果说,萨宾娜这时把熨斗搁在一旁,并欢腾地加入三个女孩的游戏中,那会怎样?如果她和女孩们一起坐在粉色地毯上,然后向她们展露自己温柔、可靠、约定俗成的母爱呢?如果她用玩具锅做饭,然后用纽扣大小的盘子上菜呢?如果她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吗?世界会因此而毁灭吗?哎呀,烫衣服时可不能一心二用,萨宾娜差点把医生衬衫的领子给毁了。
每当萨宾娜烫衣服时,她都会玩游戏,一个无伤大雅的游戏。想玩这个游戏,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它只存在于思维中,因此没人会察觉,也很难与人分享。我尽量给大家解释一下游戏规则吧:
萨宾娜把自己想象成粉色地毯上的芭比娃娃。她曾在地毯上躺过,所以她只需回忆一下躺在上面的感觉即可,地毯软硬适中,她的后背与粉红色的绒毛亲密接触。她也闻过地毯的气味,至今还清晰记得化学合成物的特殊气味。她还记得,从地毯的视角看世界的感觉,从桌椅腿、柜子下箱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世界会顿时变大许多。从下往上看,还能看到小女孩们粉嫩的小脸蛋,听到她们的窃窃私语,这不是成人的语言,而是属于孩子的语言,声音既幼稚,又有点不拘,她们每吸一口气,都带进不少绒毛,每呼一口气,都散发着苹果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萨宾娜能感觉到,她们正在用手,用柔软的小手和纤细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的身体,这种感觉就像是小麻雀的小脚丫踏过雪地,像小猫咪用软绵绵的肉掌踩奶。她们用稚嫩的小手慢慢把萨宾娜的围裙系上,又解开,把脖子那儿的领子系好。此时此刻,萨宾娜感觉整个世界都缩小了。世上的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稍纵即逝,像从坏了的水龙头滴下的小水珠,每一粒都有不同的形状。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虽然确定能发生的并不多。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萨宾娜享受着女孩们不间断的爱抚,她的身体也顿时重获知觉,她现在能清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就像一幅世界地图,流淌着河流,四处布满湖泊和海洋,高耸的山脉拔地而起,万马奔腾于大地之上,象群呼啸于森林之中,既有沙漠的炎热干旱,也有极地的凛冽寒风。
突然,一阵寒颤席卷而来,如电流般传遍全身,唤醒她肌肤上的每个毛孔。她手里拿着熨斗,肌肉逐渐松弛,变得软绵绵的(她赶紧把熨斗放回到安全的地方),她额前的头发也仿佛立了起来,她能感觉到头发的存在,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每根头发的生命力。三个女孩子正在给芭比娃娃穿衣服。
所有衣服都熨好后,萨宾娜就做完今天最后一个活儿了,晚餐的开饭声刚好传来。这时,有人按门铃,应该是邻居来接两个小女孩回家吃饭了吧。家长们在门前聊了一会儿。
萨宾娜把钱塞进运动服口袋里,带上自己随身带的塑料购物袋,准备到小瓢虫超市(波兰平价连锁超市)去买点吃的。周六做饭需要鸡肉、人造黄油和几块面包。
“哎哟,咱们家孩子可爱吃面包了,”萨宾娜出门时对尤拉笑着说,互相道别后,萨宾娜独自离去,传来鞋底摩擦小石子发出的沙沙声。
“萨宾娜!”尤拉呼喊道,声音里带点犹豫,“萨宾娜……再过几天你就不用再来我们家干活了(萨宾娜眉头皱了起来)。我和丈夫商量过了,这不快过节了嘛,你可以许一个节日心愿,或者其他心愿,我们会满足你的愿望。但你要许一个可以实现的愿望噢。”尤拉赶紧补充道。
萨宾娜一脸疑惑,歪着头用迟疑的目光看着尤拉。
“肯定有些东西,是你想要的,你自己想要的,不是你那五个儿子,而是你自己。”尤拉解释道。萨宾娜露出笑容,害羞得脸都红了。幸好那时天色已暗,没人看见她的脸颊已经像红菜一样红了。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不必多说了,但还是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些细节。萨宾娜回家后,和孩子们仓促解决了晚饭。饭后,她洗了煎馅饼的锅,检查孩子们的书包里有没有吃剩的三明治,孩子们把玩具扔得满地板都是,同时还在玩扔叉子游戏,一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刚铺上没多久的格子桌布也因此被弄脏了。这些细节应该足够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萨宾娜换上了新买的孕妇裙,干净舒适,芳香扑鼻。她还染了红头发,扎了个蓬松的包子头。尤拉开门迎接萨宾娜,今天尤拉的穿着稍显正式。萨宾娜的容貌发生了改变,这出乎尤拉的意料。她给萨宾娜倒上一杯橙汁,问道:“怎么样?心愿想好了吗?”萨宾娜卖了个关子,说等她打扫完毕之后再说。甚至连M医生也来凑热闹,手里同样拿着一杯饮料。
“我们已经知道检查结果了。”萨宾娜正把脏碗碟放进洗碗机,尤拉在一旁挑逗道,“你竟然不想知道,如果是我怀孕的话,我肯定想马上知道检查结果。”医生夫人不容许任何尴尬的沉默,分享起自己怀卡齐娅时的经历。任何一个女人,迟早都会给别人讲类似的故事,怀孕时有什么感觉,分娩时疼不疼。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
萨宾娜去打扫浴室了,尤拉终于放弃了,不再尾随,她的声音也淹没在偌大的宅邸中,萨宾娜抬起双臂,闻了闻腋下,注视着镜中的自己,用软纸巾擦拭了一下自己油光发亮的额头。她还有活儿要干,不能像平常一样对每一件事情都过度专注。她甚至忘了,自己刚才已经刷过一遍浴缸。
她走进卡齐娅的房间,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打扫,但是今天有点特殊,她觉得她好像在为自己布置房间,为自己铺上只有她才能看到的粉色床单。今天的熨烫工作也十分顺利,嗖嗖两下就烫好一件衣服了。萨宾娜一边唱歌,一边往医生的衬衫上洒水,衣领那儿发出嘶嘶的声响。
因此,正如她所计划的,她很快就做完了家务活。小女孩们像以前一样,坐在通往卧室的楼梯上,制定游戏规则,抽签决定每人要扮演的角色。萨宾娜从楼梯上看着她们可爱的小脑袋,就像小天使,小鹌鹑,春天榛子树的絮条,杨树毛茸茸的种子。
萨宾娜看得出了神,才想起自己要到楼下的厨房去。尤拉指间夹着一根香烟,正在读杂志,看起来像是童话里给人实现愿望的巫女,一直在等着萨宾娜的出现。同时,M医生也加入进来。
“怎么样?现在可以揭晓了吧?”尤拉问道。于是,萨宾娜坦白了自己的心愿。声音里充满着勇气,每说一个字,都显得更有自信。她腰板笔直,身材比平常更挺拔。
听罢,尤拉心想,好吧,怀孕的女人无论有什么愿望,都应该满足她,否则会遭报应的。
萨宾娜的心愿如下:她想和小女孩们一起玩,想变成她们手中的娃娃,躺在地毯上,任由她们抚摸自己的身体,任由她们玩弄自己的头发,她们可以随便松开自己的发箍,或者在她脖子那儿戴上丝巾、系上裙带,她还想让女孩们给她穿衣服,脱衣服(你们看,她为此还特意穿了件毛衣来),她想让女孩子们抚摸她的手臂,把耳朵贴到她的肚皮上,聆听她呼吸的声音。
“我有预感,这次又会生个男孩,”萨宾娜对M医生坦白道。萨宾娜想要的是小女孩般的温柔,想聆听她们美妙的歌声,但不是从远处听,而是像在听耳语,她想成为她们手里捧着的娃娃,巨大的、温暖的、顶着大肚子的芭比娃娃,这种娃娃在玩具店里可买不到。
此外,萨宾娜虽然不知如何组织语言,但她的确曾感觉自己像一件任人摆布的物品,如果想要继续在世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在教堂里再多举行一次圣餐仪式,毕竟一次圣餐不能确保自己获得救赎。人要敢于面对自己最大的弱点,才能变得愈发强大。因此,萨宾娜想躺在粉色地毯上,换个角度观察房间里的家具,偷窥沙发床和书桌底部。通过这个视角,所有物品看起来都像苍天巨树,所有人都萎缩成穿着拖鞋的两条腿。当然,她还想回到以前不解人言的懵懂状态。
最后,她还补充道,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她的心愿感到惊讶,更不要取笑她,如果这个愿望实在难以实现,那也没关系,就当她什么也没说过,她还告诉大家她想要一瓶脉动牌抑汗喷雾,或一件新的孕妇紧身裤,银戒指或印度商店买的裙子也可以。
M医生忍不住大笑起来,差点拿不稳水杯,尤拉生气地不断使眼色,他才勉强按捺住。尤拉久久地注视着萨宾娜,表情十分严肃,双唇紧绷,嘴角颤抖。她一言不发地把萨宾娜领到楼上去。终于,萨宾娜的脸上泛起了红晕,那是一种牡丹或玫瑰的红,罂粟或葡萄酒的红,或者是舌头般的红,如同她肌肤下的五脏六腑。
林歆译点击“阅读原文”订购世界文学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ougeccar.com/ddqh/5087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