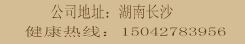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法国恐袭频发,两学生为欧元ldq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法国恐袭频发,两学生为欧元ldq

![]()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法国恐袭频发,两学生为欧元ldq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当地气候 > 法国恐袭频发,两学生为欧元ldq
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不来一次“刮骨疗伤”不行,可拿起了刀子,又该从哪儿下手呢?
10月29日,法国尼斯市中心的圣母升天教堂发生恐袭事件,一名持刀袭击者将一名女子斩首,并杀死了另外两人。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期间多次喊叫:“真主至上”,警方表示:“杀人手法与孔夫朗-圣奥诺里讷教师萨缪尔·帕蒂被杀害的方式一样。”
01
学生成为斩首老师的帮凶
10月16日,47岁的巴黎历史老师萨缪尔·帕蒂在巴黎北郊被砍头,世界惊恐:这还是我们向往的自由巴黎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1日报道,帕蒂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具有争议的宗教漫画,他出于谨慎已提前告知信教学生,如果感到不适可以先行离开教室。尽管校方事后邀请部分家长商谈此事,但一名学生的家长仍感到不满,接连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文字,强烈要求帕蒂被革职,并指明了学校名称和地址,以及涉事教师帕蒂的身份。
尽管得知帕蒂的姓名,但由于没有与这名老师接触过,凶手安佐罗夫向两名学生支付了大约欧元,来帮助他确认。凶手还告诉学生们,他只想“让这位老师为漫画一事道歉”,并且只想“羞辱他,打他”。检察官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4岁和15岁的学生向安佐罗夫描述了帕蒂的长相,并在校外和他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的老师出现,导致帕蒂被斩首。事后,凶手在推特上拍照炫耀:“以安拉之名,我处决了一条胆敢冒犯穆罕默德的地狱猎犬。”因拒捕,安佐罗夫被警方击毙。
马克龙也来到了老师葬礼现场
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涉事家长在网络上的“仇恨宣传”,直接导致了之后的斩首惨案;警方也认为,凶手杀害帕蒂是受到了视频内容的煽动。
视频也成为了“帮凶”。难道视频这种媒介真会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
令人倍感不安的是,法国的恐怖袭击越来越多的来自身边,源于“内部”,而非“输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后恐怖主义将越来越难以防范,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平日里温和有礼的穆斯林,他可能是你的邻居,转弯角的超市老板,或者昨晚还在跟你酒吧谈论哲学的知识分子,突然间就会变成恐怖分子加害于你。
这才是未来,最可怕的问题。
02
对暴力事件的思考有用吗?
这一案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也加强了对极端分子的打击力度。
令我们不安,并陷入疑惑的是,一、两学生为何为了欧就可以让老师丧命?二、法国为何接二连三地爆发恐惧事件?
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到2名武装恐怖分子袭击,杀害了包括多名漫画家在内的11人。而就在同时,巴黎东部再掀枪案,枪手冲入一犹太超市劫持多人,并对警方喊话要求释放前述两名嫌犯。随后,警方强力进攻,两起武装劫持案中的3名嫌犯被击毙,另一嫌犯在逃。一场法国5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牵动全球目光。
年巴黎民众抗议《查理周刊》被袭
事发前两小时,《查理周刊》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用漫画形式揶揄了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这刺激本来就已严重的法国极右情绪,成为此系列暴恐事件的导火索。
11月13日,巴黎餐馆、音乐厅和体育场等多个地点遭枪手和炸弹客袭击,导致人遇难。
年法国国庆日,在南部城市尼斯滨海大道上,原籍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莱勒驾驶一辆载重卡车对人群进行碾轧,造成84人死亡,人受伤。IS宣布对此恐袭案负责。法国官方认为,31岁的布莱勒很可能是新近发展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年4月,巴黎最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遭袭击,导致警察一死两伤,袭击者被击毙,IS宣布对此恐袭案负责。
法国穆斯林
年10月,4位法国警察被身为穆斯林的同事持刀杀害……
近些年,法国可谓是恐袭重疾缠身,恐袭一次次击穿了民众的心理底线,成为法国历史上的“寒蝉”节点。
法国右翼政治家菲利浦·德维利埃在《到了说出我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了》中写道:“痛苦这个词包含了法国本身。法兰西就是从痛苦中诞生的。”法国极左翼联盟领导人梅朗雄在facebook上留言:“荒谬的屠杀又回来了。我们要为同胞深切哀悼,感同身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到我们生活在人道主义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又让人感受不到什么人道主义。”
这些是无奈之言,很悲伤,但又是现实。
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穆斯林人口大量攀升,“多元文化共存”的失败,政策上的无奈,地缘区位以及安防的低效等因素,加上一年来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衰退,失业加剧,以及人们交流受阻,压抑情绪到了冰点,这些构成了法国多次遭受暴力事件的软肋。
03
政策上的无奈
马克龙总统发表演讲,号召全法国民众团结一致、行动起来,铲除“极端伊斯兰主义祸根”:“伊斯兰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处于危机之中的宗教,这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才存在的现象。”他的此番表态引发了全世界穆斯林群体的愤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被激怒了,上次他让马克龙去查查自己是不是“脑死亡”,这次讽刺马克龙需要接受“心理健康检查和治疗”,因为他“像巫婆一样追捕穆斯林”。法国愤怒回击称,埃尔多安的言论“不可接受”,并以召回该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方式向埃尔多安发出“强烈信号”。
在法国,已经显示:弗朗西斯·福山梦想的全球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走到尽头;还有,我们要认识恐袭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一小撮,还是已经形成势力?遗憾的是,法国当政者迟迟无法找出恐袭的本质,形成行之有效的安防策略。
实际上恐袭的原因不是现在才有,是长期以来,一点点累积成疾的,安防策略也做不到一刀切——悖论永远是我们生活的难点,这不是智慧一下子能解决得了的,共存而改善安防策略也只是历届政府能做的事儿。
追溯欧洲恐怖主义灾难的源头,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颠覆了萨达姆政权,以及伊拉克的政治势力结构和脆弱的中东力量平衡。
自伊拉克战争开始,法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所有军事行动,独自实施了对马里、几内亚等地的清剿。萨科齐为拉选票而使用一式“昏招”——成为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急先锋。临终前的卡扎菲预言:“北约的人们,你们听好了!你们正在炸毁阻止非洲移民去欧洲和阻止基地阻止恐怖分子的一堵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正在破坏它。你们这群蠢货,你们将会因为上千的非洲移民在地狱中燃烧。”难道法国没有一人意识到这话背后的指向。
几乎在介入利比亚的同时,法国率先与叙利亚断交,并承认反对派是唯一合法政府,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随着各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叙利亚陷入全面内战。ISIS开始由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借助战乱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头号恐怖组织。
若IS论功行赏,美国稳坐第一把交椅,法国将位列其次;但如果按受害程度来排序,恐怕法国要独占鳌头了。因此,法国一次次遭受恐袭是往日张狂的回报,是在为过去的错误政策买单。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他们的恶性不过是对欧洲残暴干预的回击。”
齐泽克04
现实不再让他们有未来
二战后,欧洲国家吸收了大量来自原殖民地的移民。据统计,法国战后吸纳移民有万人之多,其中许多是穆斯林移民。当今,法国穆斯林人口达万,约占总人口的11%。近来,反欧盟、反移民的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民众支持率正稳步上升。年,约有18%的人表示认同国民阵线的主张。这个数字逐年增长,已达到34%。
法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对移民采取多元文化政策,就意味着各个独立的体系会在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保持原有特色,这就形成了交流障碍。于是,法国官方为了让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要求他们按照法兰西标准改变自己的传统。这一点上,开始向美国“熔炉政策”靠拢:无论你来自何处,到了美国就要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
年,法国颁布禁止遮盖全身、仅露双眼的“面纱禁令”;年4月,法国一所学校两次禁止一名15岁的穆斯林女孩进入课堂,原因是她穿了黑色长裙;11月,右翼政治家利用学校的“培根+肉肠”餐来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个法国人”。
年夏季号《外交》杂志上,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已经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法国社会政策是有问题的,让社会更加分裂。
法国青年的激进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15年来,人类学家都娜·波扎尔一直在
但法国不同,法国是一个地中海国家,与北非隔海相望,而北非也是伊斯兰恐怖势力的重要基地。地中海的气候条件本就相对温和,加上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漫长,这使得外来恐怖分子更容易偷渡进入法国;而法国与北非的地缘关系的紧密,也意味着文化传播相对便捷——资料显示,法国是除俄罗斯之外第二大IS欧洲圣战分子提供国家,在为IS效力的0多个欧洲圣战分子中,有至少个是法国人。
06
无能的法国警察
法国原有四大警察机构:负责城市治安的国家警察局、负责乡镇地区安全的宪兵队、负责社会安全情报和国内反恐活动的普通情报局及负责反间谍和国外反恐情报的国土警戒局。
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法国人口流动剧增。分属国防部的宪兵队和分属内政部的国家警察局之间,针对人口管理的信息交换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同时,宪兵自身的情报机构也存在种种缺陷,最典型的问题是各地区宪兵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机制,仍停留在依靠人际关系的自发式配合模式。
大名鼎鼎的“普通情报局”历史成就辉煌,但是,由于经常被执政党操纵执行刺探反对党的活动,普通情报局背上了“秘密政治警察”的恶名,在年改革中被各派政治势力齐心协力地“埋葬”掉了。之后,国土警戒局被扩充成了国内安全总局,同时担负起维护国内安全秩序和反恐的任务。
由于习惯于反间谍式的工作模式(在特定的领域内对小范围的目标进行监控和追踪),国土警戒局在接手原先普通情报局广布于法国各地的分支结构之后,需要对社会不同层次和群体进行大范围调查和跟踪,面对国内社会安全监控活动中汹涌而来的巨量情报素材,工作人员总是焦头烂额,效率低下,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
07
法国将在2年被伊斯兰化
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米歇尔·维勒贝克出版的第六部小说《臣服》,预言法国在2年将全面伊斯兰化——届时法国总统奥朗德已是第二任期完后下台,一个属于穆斯林的党派坐在爱丽舍宫的宝座上。
书名《臣服》显然是对“伊斯兰”的暗示,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指的是对上帝意志的臣服。主人公弗朗索瓦是一个大学文学教师,在他的眼中,法国社会党、人民运动联盟两个左右大党派与一个名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党派合为一个政体,中间派领导人贝鲁成为法国总理(而在现实中,贝鲁是中间派的民主联盟主席)。
弗朗索瓦和一个女大学生同居,女友去了以色列,他勾勒出2年的法国:波斯海湾的君主国们向法国的新伊斯兰学校注入大量资金;女性再也不敢袒露小腿;失业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女性都从工作场所退出……
面对社会的突变,弗朗索瓦无可奈何。他试图继续寻找自己的信仰。从他自己喜欢的小说家足迹中还可以找到天主教的踪迹,而自己要想再回到索邦大学,不信伊斯兰教已行不通了,因为索邦大学要求教师皈依伊斯兰教。最终,弗朗索瓦臣服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一夫多妻;二是工资涨了三倍。
恐怖袭击案时上市的最后一期《查理周刊》头版刊登的是维勒贝克的漫画头像,画中人物说“年,我开始掉牙,2年,我就要过伊斯兰斋月”,在另一幅漫画上,这位作家说,“年,伊斯兰国组织将进入欧洲”。
法国《巴黎人报》评论,维勒贝克的新作描述了一个可恶的反面英雄人生选择。这个虚构的政治格局让读者会出一身冷汗,令人感到既恶心,又郁闷。该报问道,这难道是法国文学在自杀?《解放报》书评写道:《臣服》在思想史的年表上标志着极右翼挤进了高雅文学的殿堂。《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本书可以被当做是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西方极右翼常做的又一场噩梦。
08
噩梦真会降临法国吗?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欧盟15个国家的0多万移民或来自外国的人口中,有一半皈依或信仰伊斯兰教。而法国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穆斯林群体——0年,在6万总人口中占到了万(有学者认为已到达万),占法国总人口10%,其中半数已拥有法国国籍。
年10月,《费加罗报》公布了其委托IFOP所做的“伊斯兰在法国的形象”的调查结果: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社区的存在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7%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完全没有或者没有很好融入法国社会,68%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当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三个词来描述伊斯兰教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拒绝西方价值、狂热、顺从和暴力。
伴随着法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越发得势。这一党派强调法国的民族主义,敌视移民和伊斯兰,反对全球化、反对欧盟。“国民阵线”党魁玛琳娜·勒庞被称为“法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曾经激烈抨击穆斯林群体,如“我觉得法国并不需要有清真寺的尖塔”,“在法国,人们不需要蒙面散步”等。
法国穆斯林社团的力量还在于其年轻,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超过20%的人则居住在富裕的地中海边,那里几乎垄断了与马革里布国家的各类贸易。但穆斯林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身处边缘,许多人抱怨在职场上普遍受到歧视。这样,使得法国穆斯林与本土法国人造成了社会的高度紧张。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名法国籍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极端组织一起作战,另有名正在前往上述区域的途中,还有名极端分子在接受军事训练后已经返回法国,他们希望将圣战组织引入法国。
09
全球资本主义是恐怖主义的
根源?
我们要更清醒地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
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包容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互相尊重彼此敏感的地方)显然是不奏效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不可能容忍我们渎神的漫画和不计后果的幽默,而这些恰恰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自由。同理,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法忍受穆斯林文化中的很多行为。”
新资本主义是一场意象的狂欢,任何“真实”都不过是这个无形体系建构的产物。“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敌人”的虚象都是这场游戏不可或缺的角色。
齐泽克谈到:“如果我们仍然在自由-民主坐标上,我们无法打败恐怖主义。悖论就是,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足以拯救他们所反对的原教旨主义的冲击。原教旨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真正缺点的反动——这就是为何它总是一次次地由自由主义引发。自由主义会慢慢破坏其本身,唯一能拯救它的是一个崭新的左派。为了让自由这个关键的遗产得以保存,自由主义需要激进左派兄弟般的帮助。这是战胜原教旨主义的唯一办法。”
尽管知识分子空谈是他的天性,但我们回味一下本雅明的话:“每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见证一个失败的革命”,回过头来想想,这话是说给清醒人听的,而反衬着一次接一次遭受恐袭的法国,革命已经过去多年,之后的法国显得如此悲怆。
要解决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不来一次“刮骨疗伤”不行,可拿起了刀子,又该从哪儿下手呢?
猜你爱看亚美尼亚会变成火药桶吗?历史的悲情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激起的战争泡沫法国圣母教堂发生恐袭事件,马克龙与伊斯兰世界交恶世俗主义真能救欧洲吗?END
撰文:我看的是人间哀愁
编辑:葵妮朵朵
主编:耶曼
为曼话空间点亮星标
曼话
MH
Space
原创不易
尽情分享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授权
我看的是人间哀愁
转载请注明:http://www.ougeccar.com/ddqh/509234.html